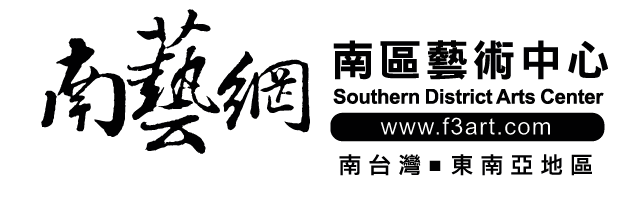推薦特蒐
傳承無釘工法 久美國小重建鄒族「赫夫」
南投信義鄉久美國小,啟用消失70多年的鄒族傳統聚會所「赫夫」,其中結構未用釘子,僅以黃藤綑紮,展現獨特傳統技法。(記者劉濱銓攝)
2022/01/05 05:30
〔記者劉濱銓/南投報導〕南投信義鄉以布農族為大宗,但在久美部落仍有少數的鄒族,在地久美國小為推動原民教育,搭建消失七十多年的鄒族傳統聚會所「赫夫」(hʉfʉ),不僅建築結構以黃藤綑紮,不用任何釘子,也讓學童參與搭建,校方昨舉辦「赫夫」揭牌啟用,重現傳統建築,傳承鄒族文化。
久美國小昨以鄒族古謠拉開啟用典禮序幕,先由鄒族長老鑽木取火,將火種傳遞給參與學童,並進入「赫夫」點燃火塘,象徵薪火相傳,隨後揭牌並圍著「赫夫」跳起圍舞。
鄒族長老安孝明表示,信義鄉鄒族相當少,為協助校方傳承鄒族文化,便運用傳統的綑綁工法搭建「赫夫」,結構未用釘子,以柳杉、孟宗竹、桂竹、茅草搭建,並讓學童參與簡單的建築工作,如夯土、堆砌火塘及搭梁等,更能加深對鄒族傳統建築的認同。
提供建物木材的林務局與台大林管處表示,近年為回復原住民自然資源權利,持續推動共管機制,盼與原住民共同守護山林、共享山林資源,尤其運用國產木、竹材建置的「赫夫」,還能作為鄒族傳統文化教育場域,相當有意義。
校方則感謝各界提供材料與資源構建聚會所,讓鄒族延續傳統文化,也使布農與鄒族能和諧共處,促進族群繁榮。
黑貓姐李美玲中年改種洋菇,種出一片天。(記者顏宏駿攝)
LIU YC -
推薦特蒐
影/職人揭「瀕臨失傳的土葬儀式」 網讚:文化需要傳承
國人自古以來有「入土為安」的傳統,過去以土葬為主,由於世代沿襲至今,增加了土葬的面積,讓許多土地不能使用來開發。近年來,除了人口膨脹,還有環保意識抬頭,加上政府鼓勵樹葬、花葬、海葬、植存等環保葬儀方式,更加速了土葬儀式失傳的速度,YouTube頻道「目映台北」紀載了瀕臨失傳的土葬儀式,指出現今有許多專門置辦土葬的師傅們苦找不到接班人,讓許多網友感嘆文化的傳承正在瀕臨消失之外,也表達對於這份傳統的尊敬之意。
有些人希望能用土葬的方式,來完成人生的最後一哩路,才能展現對死者的尊敬。隨著時代變遷,喪葬的儀式與場所也產生了變化,土葬在執行面上耗時、也耗力,每一個流程都不容馬虎,從接板、小殮、勘輿地理風水、開光解結辭神、敬祖、拜門口(小施)、跑赦馬、過金橋、牽亡陣、永靖弄鎦、哭路頭等,之中包含了許多即將失傳的喪葬陣頭與儀式,如今更是少見於世。
片中收錄了許多資深禮儀工作者的訪談,龍福禮儀公司的職人林奕華表示,自己本身從事殯葬業已經20幾年了,他的爺爺在生前交代過他們,如果他走了,一定要將他「土葬」,如果將他「火葬」,大可不必去祭拜他了。由此可見,老一輩的人,對於「土葬」喪儀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重視,以表達對於往生者莊重的儀式感。
有許多網友看完影片後,紛紛表示「把喪禮拍得如此有質感」、「文化需要保留」、「學到很多傳統知識」,不過現在人普遍追求簡單的方式來舉辦喪儀,環保葬也成了如今的趨勢,在傳統和新世代之間的改變歷程中,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選擇和考量,在社會上也有不少人堅持要用土葬來圓滿人生的最後一程,縱使土葬瀕臨消失,仍有許多老師傅期盼能傳承給下一代,讓這項習俗能夠繼續存在著。
《民視新聞網》提醒您 :民俗傳說僅供參考,請勿過度迷信。
LIU YC -
推薦特蒐
米莎的客語歌曲創作如何帶她回家
客家創作歌手米莎。(圖/山下民謠提供)
Text by 米莎|苗粟三灣人,2006年開始音樂創作。發行專輯《戇仔船》、《百夜生》、《在路項》、《河壩》。2020年獲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最佳客語歌手獎。
我想從一條河說起。
河流輾側,從山間到平原、從清晨到黃昏,迂繞流過苗栗縣北部六個鄉鎮:南庄、三灣、頭份、造橋、竹南與後龍。設若它是聲音的載體,那麼它實實地錄下了賽夏、海陸與四縣腔的客家,以及閩南的歌謠與故事,當然也有華語,而早期在其中以客語為大宗。
河流在我未有記憶的很久很久以前就存在了,祖輩的生命與死亡像許多微細血管支流溶入其中;它也像一條話語的河,款款擺擺,流入我的童年與往後離家的歲月。
找到自己的聲音
大學時代,與好友組成樂團並初試創作,由於彼此年紀相仿、生活經驗雷同,當時總覺得自己的華語作品並沒有屬於自己的形貌。因為某個契機,開始嘗試用客語寫歌詞,離家在外求學數年,始終待在聽不見客語的環境下,這語言直接跳越時空,連結家鄉的人事物,歌曲也因此有了記憶的厚度與重量,有了與他者不同之處。
這首關於家鄉河流的歌,讓我找到自己的聲音與樣貌。我的母語並不只客語。父親是苗栗三灣客家人,母親是雲林斗六閩南人,因為從小徙居客庄,客語是我最早熟悉的方言。
方言具有一種活跳的特質。早期客家以務農為眾,語言裡龐大的區塊和天時、節氣、耕種收穫、自然環境相關,當我將父親說過的老古人言諸如「 驚蟄先響雷,七七四十九日烏」【註1】、「河溪直,芋仔好食」【註2】放進作品中,這些歌曲一下子落地生根,不再面容模糊。
因為上頭堆疊了數十數百年的生活經驗,連結到不同季節的風與光線、水井與河流、水稻田與茶園、祭祀與生死儀禮,連結到一個集體的「原鄉」,不再只是單一個人的生命經驗。
在這個時期,我大量聆聽許多以客語創作的現代作品。從美濃反水庫運動【註3】開始合作的鍾永豐與林生祥,陳述農村與現代社會碰撞的情態,草根、直白卻又蘊含深意,極耐嚼的語言裡同時包容個人困境與一種通盤的、跨越時空維度的思考。
在天地山水人情間不著意畫出失落樂園,卻始終展現人的自由與悠然的陳永淘;羅思容細緻的歌詩吟詠,在巫的神祕呼吸之間,女兒、母親、與大地媽媽一起歡愉舞踊;反骨帶勁滿滿實驗性的劉劭希、用山的大器唱著都會氣息的謝宇威,還有黃連煜、顏志文⋯⋯。
前輩們像是一座座崇高山嶺,各有精采的風姿與路徑。那麼縱有河流的血脈,它要引我流向何方?才藉著方言書寫固著了根,我就意識到這很可能成為往下一步前進的阻礙,如果我的目光始終停駐在水田與茶園。
像河流那樣流動
起初是一個建立原點的過程,透過作品量測與他者、與家鄉的距離,找到自己的原點,是為了能有一個觀看世界、發出聲音的視角,而那個「世界」,無疑在外頭、在路上。
離家之後,我一直在移動,從台北到台南、台東,甚或遠至中南美洲,在路上的時間遠多於靜止不動的時間,遇見的人事物不斷累積,成為作品的材料及養分。如果我不是山,那就自由地當一條流動的河,經過許多地方、看見許多風景;如果無法像山那樣唱歌,那就像河流那樣唱歌、唱一直在路上的歌。
這其後有幾年,除了繼續輕盈地在路上移動,因緣際會有了一些為孩子寫歌的機會,離開自己相對熟悉的領域,為不同年齡層的聽者與歌者創作。當時鮮少與小孩相處的經驗,創作小孩的歌起初是個大難題,除了回想自己的兒時往事,也嘗試把自己拉回孩提時光,用孩子的視角看世界。
小孩的世界沒有成人的許多框架,在創作時,我找到一塊全新的領域,驚喜發現向來過於工整的書寫習慣被拆解了,句子的長短、換氣呼吸、節奏都與自己原先的作品有明顯的區別。
在錄音時,我發現小孩的學習能力很令人驚奇。參與製作的音樂人有南北腔調差異,聆聽錄製完成的作品,發現同一群孩子竟能維妙維肖地模仿各個音樂人的腔調,分毫不差。發音、咬字、用詞這些過去我在自己的創作領域裡並不特別講究的東西,透過孩子放大之後,讓我意識到各種形式的創作都必須「精準地傳達正確的事物」。
除了作為一個學習的契機,這也促使我開始思索每一世代獨有的養成與氣質。在客語創作的路上,清晰可見前輩音樂人的軌跡,他們的養成環境是相對閉鎖的,他們的腳真切地踩在土壤裡,他們的客語是深根的,在那樣的縱向基礎之上,往上生長發枝展葉。
我的世代更多的是橫向擴展,網路帶來資訊流,讓同一世代的創作者可以接觸到幾乎相同的訊息,快速且幅員廣闊,但除非刻意挖掘,幾乎沒有縱深,更遑論這個世代的長成,客語的生活環境與使用機會少了太多。
那之後我離開一直以來「在路上」的狀態,從台南搬回北部山區靠近老家的地方。十年的創作過程,越到後期越感覺到:儘管在南部住了十幾年,我的作品就是沒有永豐與生祥歌曲裡那種南方溫潤的大氣,就是沒有銘祐老師那種來自400年繁華古都的「市」的氣味。後來從朋友那邊聽到甘耀明老師的說法,我就懂了。
甘老師說,北部的山很魔幻。
向魔幻的山洄游
丘陵地帶多山、天黑得早而瀰漫著魔幻感,那些在黑暗中看不見的東西,從小浸潤著我的成長,已經內化不可磨滅,簡言之是一種「鬼氣」。我所寫的每個文字,鋪成軌跡指向我離開已久的山,原來我的每首歌,都跑回北部的山裡去了。
2016年,我在峨眉山區,農曆7月半前後,用11天完成新專輯11首詞曲,每日每夜寫作的時候,屋前屋後的生靈與氣息圍繞著我,這些歌曲吵鬧著說它們想被寫出來,那個狀態用起乩形容也不為過。
寫歌十年,這個時刻我突然感覺到真正進入客語的創作裡了,彷彿初次感受到用客語寫作歌詞的樂趣,像是諧音字的使用、語言的美感、畫面到語言的轉換、語言到曲風的融合,都是自然而然。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對這個創作工具是稍稍能夠掌握的。從沒想過我選擇的創作語言會真正帶領我回家,簡直就像是這個語言要求我給它一個它想要的生長環境。它是活生生的。
在那之後,2019年我製作以傅柯「愚人船」(Narrenschiff) 概念【註4】為主題的專輯,傅柯以流行疫病探討文明與瘋癲、同質與異質、主流與邊緣之間的人類心理與哲學,要用或許屬性更為農業、更為生活化的客語傳遞哲學思想似乎難為,卻反而讓一切皆是可能性。
方言的活跳性質讓我可以更無框架、更自由地使用字句去創造隱喻、創造超現實的空間、找到潛意識與意識、夢境與現實之間的通道,它本身具有的質樸也讓一個字詞更可能帶有多層涵義與色彩,更富詩意與想像力。
沒有人告訴我這可行,但也從來沒有人說這不可行。我想起家鄉的河流,它有時氾濫,有時平靜,從不懼怕陌生的流向與嶄新的面貌。
我夢見一條河流。它從很久以前就存在,許多人的話語和夢境、生命與死亡成為支流灌注到河水裡,河流流過許多崇高的山嶺,流過平原蜿蜒向前。河流漂送我離家,向陌生之地探索,隨後又牽引我回來尋找它,現在它輕輕承托起靈感與思想的船楫,一如昨天和先前的每一天,穩定又豐沛地前進著。
【註1】老古人言是客家對俗諺的稱呼,此句意指若還沒到驚蟄節氣就聽見雷響,將連下多日雨水。
【註2】秋天銀河呈現南北向的時候,芋頭就可以收成了。
【註3】1992年10月,美濃獲報消息,得知政府預備興建美濃水庫以提供高雄地區用水,於美濃水庫壩址位在斷層之上,建設有安全疑慮,且會嚴重破壞黃蝶翠谷熱帶母樹林之生態,以及衝擊村落內維持已久的傳統客家文化等因素,由曾貴海、鍾永豐等人籌組美濃愛鄉協進會,並在1993年率美濃客家鄉親搭乘夜行巴士,遠赴臺北抗議。
【註4】法國哲學家傅柯於1965年出版哲學書籍《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中提出的概念,藉由中古世紀歐洲於黑死病與痲瘋病流行之際發展出來將病患隔離的船隻,探討文明社會對異質人事物的排拒。
插畫/Cecil Tang
原文 / verse / https://www.verse.com.tw/article/misa-musician
文字 /米莎
圖片 /山下民謠提供
編輯 /游千慧
核稿 /蘇曉凡
LIU YC -
推薦特蒐
天上漂浮的小小宇宙:黃聲遠如何建造台北植物園的新溫室?
第一期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以下簡稱方舟計畫)中,因應台北植物園位於首都,展示保種植物的定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以下簡稱林試所)委託建築師黃聲遠領軍的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翻修、打造溫室區。
黃聲遠從小到求學過程都在植物園附近長大,也常到植物園看溫室。隨著年歲增長,對植物有了更多感情,收到林試所的委託,重新踏入植物園,卻驚覺位處都會核心的植物園內,歲月沖刷的溫室群,看起來有味道,卻也顯得陳舊委屈。
「走進溫室區時我是很心疼的。這群專業科學家竟然能容忍積水等問題,只希望可以給他們一個地面不泥濘、不會滑的工作空間。」黃聲遠注意到,溫室區域周圍是十至12公尺高的樹木所構成的空間,除中央圓形溫室外,還有六角溫室、長形蘭房等數座保留日治時期地基的小溫室,加上每日辛勤工作的園丁及植物,像座村落,形成植物園恆常不變、令人懷念的風景,「是一種老朋友在那裡生活的感覺。」
看過環境後,田中央團隊把整塊地當成一間大房子來設計。除了拆除結構老舊已成危樓的圓形溫室(並預計留下斗拱作為紀念),以及溫室棚架區仍有待設計外,周邊的小溫室和容易積水的地面,只進行小幅度的翻修,如:拆除六角溫室的紗窗、清潔玻璃、重新鋪設地板材料、處理排水問題等。黃聲遠笑談,「叫他們盡量丟出各種奇怪的想法,他們都想不出來。除非做出比他們想像得更體貼的東西,他們才會提出更多需求。」
「受脅物種中,日常容易取得的花草反而是最危險的,受到保育的喬木等大樹已經被保存在植物園裡。」方舟溫室計畫專案經理、也是團隊建築師的蘇子睿說,設計溫室時特意用溫室棚架把視線壓在十公尺、略矮於喬木群的高度,使周圍的喬木融入溫室區的立面景觀,行走穿梭時,也能看見樹冠和藍天。
「國中時來植物園寫生,對圓形溫室和前面的長方形荷花池印象很深。所以也在原本的位置,用圓弧棚架再現那個圓形穹頂。」蘇子睿說,團隊盡量保留空間原來的分割秩序,走進溫室棚架建築,左側的降溫溫室內,預計用水簾、風扇和頂部模擬林間斑光的採光設計,來製造各種溫、濕度與日照狀況,讓全台灣的植物都可以找到適合的角落安置。
長形荷花池的兩端則化為左右兩座較小的恆溫溫室。梯形延伸的棚架下方則設計數個直徑不同的圓,從地面到柱子都能展示植物,也提供遮蔭,適合校外教學圍坐導覽。黃聲遠回憶:「植物園很少遮蔽物,以前到植物園來,只要一下雨,遊客四散奔逃,只有小天壇或南海劇場幾個零碎空間能躲。」
約二樓高度的鏤空圓弧構造貫穿整個溫室棚架區,頭尾的圓弧如軌道,中間開花般散放著大小圓形。團隊在有機的環境裡加入幾何的呈現,跟舊有的東西排列在一起,意外呈現和諧秩序。蘇子睿說,某天他和實習生一起拍攝這座模型,突然湧出的念頭竟不謀而合:「好像宇宙一樣。」
「以後走到這裡,就可以看見天上漂浮著一個小小的宇宙。」黃聲遠相當滿意這個抽象的構造,「植物園和以人為主,用來欣賞的園林不一樣,這裡把植物當成主角,面對而不是消費它們。這個小宇宙裡,背後隱約可見知識體系,又不希望被既定概念框住,到處都是開放式的出口,這才是最迷人的地方。」搭載落難繁花野草的方舟,航進以植物為主體的鋼骨宇宙。這麼袖珍的溫室,可以代表首都的植物園嗎?
黃聲遠聽了林試所的規畫,起初也不可思議,然而放手去做後,設計者以體貼細膩的思維,保留了最大的使用彈性,使得台北植物園即將搭起的空間,更像是一座植物的劇院、美術館或一座舞台。在黃聲遠的想像中,在這裡可以邀請植物當主角,言說自己的身世。被亡羊補牢、誠心保留的珍稀綠意,若能在這片微型宇宙靜謐存續,比人類短暫的介入更悠遠漫長,此時畫下的結構,或許即是某種隱喻。
原文 / verse / https://www.verse.com.tw/article/green-island-sheng-yuan-huang
文字 /任容
圖片 /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編輯 /吳哲夫
核稿 /游千慧
LIU YC -
推薦特蒐
景觀建築師吳書原的荒野倡議:讓野草美學成為日常風景
吳書原是野草美學的歌頌者。(圖/宋修亞攝影)
以台灣原生種作為景觀設計的浪潮,近年猶如強風吹拂,從公共景觀到私宅都開始有劇烈變革。在景觀建築師吳書原的作品,一次次成為大眾關注焦點,從早期的陽明山美軍俱樂部、臺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到近期的松菸「不只是圖書館」澡堂花園、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空總C-LAB)景觀設計以及桃園永安漁港海螺、橫山書法藝術館等,少了爭奇鬥豔的色彩, 卻建立了不刻意雕琢的野草美學。
攤開吳書原的日常,爬山、潛水都是心頭好。作為野草美學的歌頌者,徜徉在大自然不僅僅是興趣,更是不愧對景觀設計專業的一種生活體現。無庸置疑,海拔3000公尺、海平面下40公尺物種都不容易見著,有幸親臨現場,體驗被包覆的五感震撼,是最珍貴的美學啟發。
「當你永遠都只去大安森林公園,你做出來的設計就是『大安森林公園』;但當你可以潛進海平面下40公尺,看到不同珊瑚的組態,就會開啟一個新想像,原來物種不用人家設計,它組合出來就是最美麗的樣子。」吳書原說:「我對海有一種探索未知的渴望,比如坐船出去看到一望無際的海,你難道都不會好奇裡面有什麼嗎?」
對景觀設計師而言,能做到的不過就是努力重現自然。
物種10000和30的距離
「當人類有一天可以到火星上去,可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回來就會做不一樣的事情。」套用在吳書原身上,赴英國就讀AA建築學院景觀都市學碩士,而後進入當地職場,七年後回到台灣,一路上也存在類似的心境轉折。
「我對台灣物種的了解,都是從英國人嘴巴講出來。」問倫敦同事的寶島印象,原來不是知名地標台北101,而是豐富的地形、氣候、植物狀態。
英國最高峰約一千多公尺,但台灣超過3000公尺山脈有兩百多座,從零至數千公尺,植被群像不斷改變,台灣無疑是世界的植物博物館,「很多物種在國外早就瀕臨滅絕、不得買賣,比如筆筒樹,但在台灣,它會在路邊自己長出來。」
然而,令歐洲大陸望塵莫及的物種多樣性,並未獲得大眾等值關注,台灣景觀設計除難逃「填補建築縫隙」角色,且植栽使用單一,「明明有超過一萬種物種,但過去30年,實際應用不到30種。」進一步探究設計風格,也一再重複應用日式禪庭、法國凡爾賽宮等舶來樣貌,令人沮喪。
在桃園永安漁港海螺實現的荒野花園,極力打造建築與植物共生下的生態多樣。(圖/吳書原提供)
不同於台灣,英國建築景觀設計案一向是以扎實研究為基礎,以台北萬華為例,設計之前,應先一一梳理當地人文、土地植被等數百年演進狀態,最終才有辦法成就屬於這塊土壤的設計,「而不是單純移植紐約某案例,讓萬華看起來像紐約。」
「台灣卻還困在這裡,我們對自己沒有自信,所以一直處在模仿表面形式的窘狀。」吳書原決心扭轉現況,回台後展開一場想法革命,彙整台灣風格之際,野草美學悄然萌芽。
台灣風格在山裡
台灣坐擁冰河時期以後,世界上最豐富的島嶼生態植物學資料庫,他解釋,這塊土地之所以能在冰河期全身而退,原因在於位處北緯23.5度,是當時地球最溫和區塊,屹立數百萬年的高山皺摺,巧妙成為物種絕佳藏匿處,就此逃過低溫暴擊,造就台灣風格。
觀察美國、英國、歐洲大陸國家,氣候條件限制下,植栽物種單一,反觀台灣物種選擇簡直是大爆發,受邀策展2018年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他,緊抓著這個「台灣價值」,透過與國家研究單位植物學專業者緊密合作,最後從現存一萬件物種中、挑出500種,如願將島嶼複雜的植物群像,濃縮進16公頃森林園區。
這股天生野味,不僅成功奪得世界關注,也扭轉台灣苗圃市場長期僵化單一的狀態。和吳書原合作的苗圃商綠生活主理人沈映仁說,對比20年前大規模種植工程樹,廠商面臨被綁標的困境,加上高經濟植栽獨霸市場,近年確實有越來越多野草系植物現蹤,需求端不再只堅持植物統一規格,已較能接受「樹木本身的高低胖瘦」;隨景觀野味意識興起,苗圃商的供應自然越趨多元。
「要保育物種,最有效的方法並不是把它鎖在保種中心或植物園,而是讓民間苗圃大量培育,這才是物種得以延續下去的力量。」吳書原說,台灣溫室、網室栽培力堅強,若善加應用農改實力,成為世界植物方舟不是夢。
因此回台十年間,除勇闖業界、學界,也投身國家建築景觀工程委員行列,吳書原笑說自己很嚴格,絕不允許重複性高的物種出現在公共工程之中。
以台灣原生植物為景觀設計主角的風潮,也開始在建築豪宅延燒。(圖/吳書原提供)
當野草美學成為日常風景
去年隨著嘉義市立美術館、空總C-LAB都市美學公園、松菸不只是圖書館的澡堂花園、水交社文化園區等一鼓作氣完工,他觀察到,不僅建案代銷跟風現象顯著,許多公共空間也開始成為網美景點,「這時民眾就會漸漸發現,原來這個才是現在的主流。」
無獨有偶,他加碼分享,有一回,西區門戶三井廣場接到「怎麼沒修雜草」的投訴電話,未料管理單位派員除草後,「結果有更多人打進去說,幹嘛除掉?」
野草美學正在發酵,能否維持荒野、而非荒廢成為關鍵。以不只是圖書館旁的澡堂花園為例,空間運維單位台灣設計研究院副院長艾淑婷分享,這座迷你世外桃源得到許多正面回饋,即便是豔陽天,仍有來訪者選擇在戶外看書,和百餘種野放植物共享日常。
實驗才是植物設計關鍵
作為亞洲第一人獲得美國多年生植物學會(Perennial Plant Association)所頒發的植物設計大賞,吳書原分享2019年赴芝加哥領獎時,論壇現場荷蘭籍植物設計大師Piet Oudolf的精闢見解:「植物設計是從實驗探索出來的,今天在這塊土地上找到什麼,我就呈現什麼,萬一以後植物死了也沒關係,死了就變成知識。」
「即使一年前種下100種植物,一年後只剩50種,那也不是什麼失敗,反而是一個成果,只要植物之間找到最穩定的平衡,那就是最好的設計。」吳書原如此補充。
去年北美館展覽「異托邦花園」撤展之際,他在宜蘭三星買了一塊地,好將植物通通移過去;之所以選擇此處,也是氣候條件使然,宜蘭土壤潮濕,無需特別澆水,天生天養,但不代表任憑自生自滅,而是以實驗作為起點,而實驗永遠不嫌多。
原文 / verse / https://www.verse.com.tw/article/cover-story-shu-yuan-wu
文字 /張喬米
攝影 /宋修亞
圖片 /吳書原提供
編輯 /蘇曉凡
核稿 /游千慧
LIU YC -
專題報導
屏東縣力推低碳家園 九如三塊村「銀」向未來
得到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銀級(最高等級)認證的九如鄉三塊村,在村長楊慧貞和環保志工隊志工及近二千名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打造農業為主「社區農園」,除種植香草、左手香植物培植社區產業,蔬果提供關懷據點食用,育成三塊村自力運作且富含人情低碳示範村里,而當人文關懷與居住的環境相融合時,環境自然就亮起來。
LIU Y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