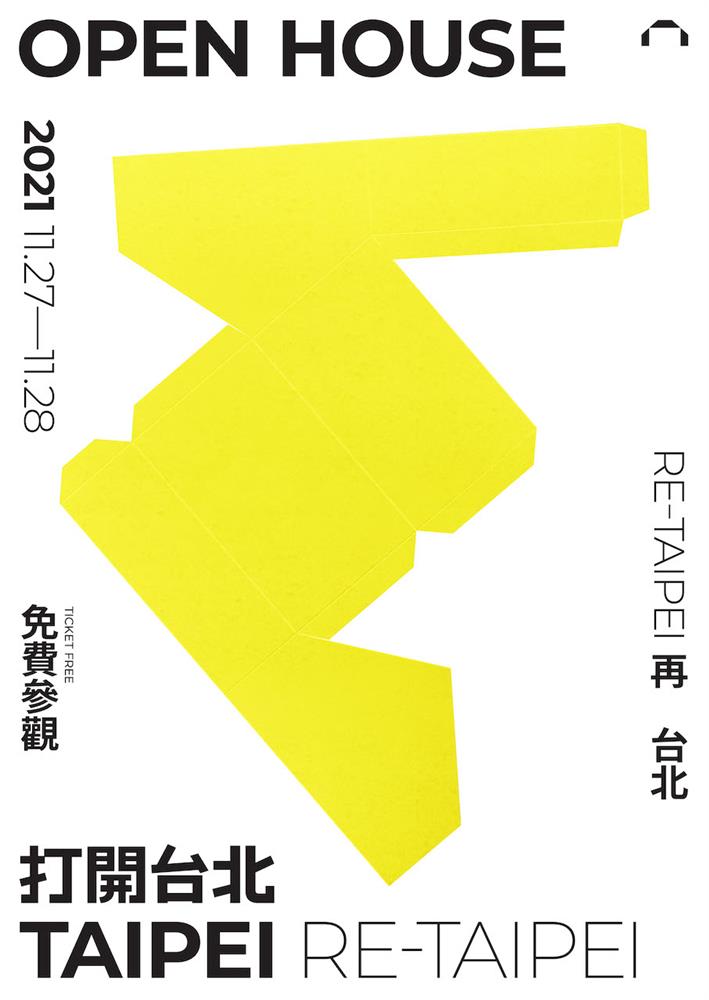客家創作歌手米莎。(圖/山下民謠提供)
Text by 米莎|苗粟三灣人,2006年開始音樂創作。發行專輯《戇仔船》、《百夜生》、《在路項》、《河壩》。2020年獲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最佳客語歌手獎。
我想從一條河說起。
河流輾側,從山間到平原、從清晨到黃昏,迂繞流過苗栗縣北部六個鄉鎮:南庄、三灣、頭份、造橋、竹南與後龍。設若它是聲音的載體,那麼它實實地錄下了賽夏、海陸與四縣腔的客家,以及閩南的歌謠與故事,當然也有華語,而早期在其中以客語為大宗。
河流在我未有記憶的很久很久以前就存在了,祖輩的生命與死亡像許多微細血管支流溶入其中;它也像一條話語的河,款款擺擺,流入我的童年與往後離家的歲月。
找到自己的聲音
大學時代,與好友組成樂團並初試創作,由於彼此年紀相仿、生活經驗雷同,當時總覺得自己的華語作品並沒有屬於自己的形貌。因為某個契機,開始嘗試用客語寫歌詞,離家在外求學數年,始終待在聽不見客語的環境下,這語言直接跳越時空,連結家鄉的人事物,歌曲也因此有了記憶的厚度與重量,有了與他者不同之處。
這首關於家鄉河流的歌,讓我找到自己的聲音與樣貌。我的母語並不只客語。父親是苗栗三灣客家人,母親是雲林斗六閩南人,因為從小徙居客庄,客語是我最早熟悉的方言。
方言具有一種活跳的特質。早期客家以務農為眾,語言裡龐大的區塊和天時、節氣、耕種收穫、自然環境相關,當我將父親說過的老古人言諸如「 驚蟄先響雷,七七四十九日烏」【註1】、「河溪直,芋仔好食」【註2】放進作品中,這些歌曲一下子落地生根,不再面容模糊。
因為上頭堆疊了數十數百年的生活經驗,連結到不同季節的風與光線、水井與河流、水稻田與茶園、祭祀與生死儀禮,連結到一個集體的「原鄉」,不再只是單一個人的生命經驗。
在這個時期,我大量聆聽許多以客語創作的現代作品。從美濃反水庫運動【註3】開始合作的鍾永豐與林生祥,陳述農村與現代社會碰撞的情態,草根、直白卻又蘊含深意,極耐嚼的語言裡同時包容個人困境與一種通盤的、跨越時空維度的思考。
在天地山水人情間不著意畫出失落樂園,卻始終展現人的自由與悠然的陳永淘;羅思容細緻的歌詩吟詠,在巫的神祕呼吸之間,女兒、母親、與大地媽媽一起歡愉舞踊;反骨帶勁滿滿實驗性的劉劭希、用山的大器唱著都會氣息的謝宇威,還有黃連煜、顏志文⋯⋯。
前輩們像是一座座崇高山嶺,各有精采的風姿與路徑。那麼縱有河流的血脈,它要引我流向何方?才藉著方言書寫固著了根,我就意識到這很可能成為往下一步前進的阻礙,如果我的目光始終停駐在水田與茶園。
像河流那樣流動
起初是一個建立原點的過程,透過作品量測與他者、與家鄉的距離,找到自己的原點,是為了能有一個觀看世界、發出聲音的視角,而那個「世界」,無疑在外頭、在路上。
離家之後,我一直在移動,從台北到台南、台東,甚或遠至中南美洲,在路上的時間遠多於靜止不動的時間,遇見的人事物不斷累積,成為作品的材料及養分。如果我不是山,那就自由地當一條流動的河,經過許多地方、看見許多風景;如果無法像山那樣唱歌,那就像河流那樣唱歌、唱一直在路上的歌。
這其後有幾年,除了繼續輕盈地在路上移動,因緣際會有了一些為孩子寫歌的機會,離開自己相對熟悉的領域,為不同年齡層的聽者與歌者創作。當時鮮少與小孩相處的經驗,創作小孩的歌起初是個大難題,除了回想自己的兒時往事,也嘗試把自己拉回孩提時光,用孩子的視角看世界。
小孩的世界沒有成人的許多框架,在創作時,我找到一塊全新的領域,驚喜發現向來過於工整的書寫習慣被拆解了,句子的長短、換氣呼吸、節奏都與自己原先的作品有明顯的區別。
在錄音時,我發現小孩的學習能力很令人驚奇。參與製作的音樂人有南北腔調差異,聆聽錄製完成的作品,發現同一群孩子竟能維妙維肖地模仿各個音樂人的腔調,分毫不差。發音、咬字、用詞這些過去我在自己的創作領域裡並不特別講究的東西,透過孩子放大之後,讓我意識到各種形式的創作都必須「精準地傳達正確的事物」。

除了作為一個學習的契機,這也促使我開始思索每一世代獨有的養成與氣質。在客語創作的路上,清晰可見前輩音樂人的軌跡,他們的養成環境是相對閉鎖的,他們的腳真切地踩在土壤裡,他們的客語是深根的,在那樣的縱向基礎之上,往上生長發枝展葉。
我的世代更多的是橫向擴展,網路帶來資訊流,讓同一世代的創作者可以接觸到幾乎相同的訊息,快速且幅員廣闊,但除非刻意挖掘,幾乎沒有縱深,更遑論這個世代的長成,客語的生活環境與使用機會少了太多。
那之後我離開一直以來「在路上」的狀態,從台南搬回北部山區靠近老家的地方。十年的創作過程,越到後期越感覺到:儘管在南部住了十幾年,我的作品就是沒有永豐與生祥歌曲裡那種南方溫潤的大氣,就是沒有銘祐老師那種來自400年繁華古都的「市」的氣味。後來從朋友那邊聽到甘耀明老師的說法,我就懂了。
甘老師說,北部的山很魔幻。
向魔幻的山洄游
丘陵地帶多山、天黑得早而瀰漫著魔幻感,那些在黑暗中看不見的東西,從小浸潤著我的成長,已經內化不可磨滅,簡言之是一種「鬼氣」。我所寫的每個文字,鋪成軌跡指向我離開已久的山,原來我的每首歌,都跑回北部的山裡去了。
2016年,我在峨眉山區,農曆7月半前後,用11天完成新專輯11首詞曲,每日每夜寫作的時候,屋前屋後的生靈與氣息圍繞著我,這些歌曲吵鬧著說它們想被寫出來,那個狀態用起乩形容也不為過。
寫歌十年,這個時刻我突然感覺到真正進入客語的創作裡了,彷彿初次感受到用客語寫作歌詞的樂趣,像是諧音字的使用、語言的美感、畫面到語言的轉換、語言到曲風的融合,都是自然而然。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對這個創作工具是稍稍能夠掌握的。從沒想過我選擇的創作語言會真正帶領我回家,簡直就像是這個語言要求我給它一個它想要的生長環境。它是活生生的。
在那之後,2019年我製作以傅柯「愚人船」(Narrenschiff) 概念【註4】為主題的專輯,傅柯以流行疫病探討文明與瘋癲、同質與異質、主流與邊緣之間的人類心理與哲學,要用或許屬性更為農業、更為生活化的客語傳遞哲學思想似乎難為,卻反而讓一切皆是可能性。
方言的活跳性質讓我可以更無框架、更自由地使用字句去創造隱喻、創造超現實的空間、找到潛意識與意識、夢境與現實之間的通道,它本身具有的質樸也讓一個字詞更可能帶有多層涵義與色彩,更富詩意與想像力。
沒有人告訴我這可行,但也從來沒有人說這不可行。我想起家鄉的河流,它有時氾濫,有時平靜,從不懼怕陌生的流向與嶄新的面貌。
我夢見一條河流。它從很久以前就存在,許多人的話語和夢境、生命與死亡成為支流灌注到河水裡,河流流過許多崇高的山嶺,流過平原蜿蜒向前。河流漂送我離家,向陌生之地探索,隨後又牽引我回來尋找它,現在它輕輕承托起靈感與思想的船楫,一如昨天和先前的每一天,穩定又豐沛地前進著。
【註1】老古人言是客家對俗諺的稱呼,此句意指若還沒到驚蟄節氣就聽見雷響,將連下多日雨水。
【註2】秋天銀河呈現南北向的時候,芋頭就可以收成了。
【註3】1992年10月,美濃獲報消息,得知政府預備興建美濃水庫以提供高雄地區用水,於美濃水庫壩址位在斷層之上,建設有安全疑慮,且會嚴重破壞黃蝶翠谷熱帶母樹林之生態,以及衝擊村落內維持已久的傳統客家文化等因素,由曾貴海、鍾永豐等人籌組美濃愛鄉協進會,並在1993年率美濃客家鄉親搭乘夜行巴士,遠赴臺北抗議。
【註4】法國哲學家傅柯於1965年出版哲學書籍《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中提出的概念,藉由中古世紀歐洲於黑死病與痲瘋病流行之際發展出來將病患隔離的船隻,探討文明社會對異質人事物的排拒。

插畫/Cecil Tang
原文 / verse / https://www.verse.com.tw/article/misa-musician
文字 /米莎
圖片 /山下民謠提供
編輯 /游千慧
核稿 /蘇曉凡